把自己作为“段子”
记者/计巍
编辑/宋建华
作为一名妥瑞氏综合征(以下简称“妥瑞氏”)患者,蛋挞的身体会伴随着不自主的抽动,以及由此带来的声音抽动。这很容易让他成为人群中的“焦点”。直到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,他发现舞台上的自己终于可以不用再费力气去遮掩这一点了。
他的那些段子说的就是自己——在漫长的时间里,妥瑞氏带给他的一个个被误解的、尴尬的、甚至是痛苦的经历。但极具反差感的是,经由喜剧的方法,这些段子,“放在任何一个普通人的场景里,都是好笑的”。
这些“好笑”的讲述也给他来一种与疾病的和解。
曾琮谕选择用演讲来直面妥瑞氏的“禁锢”。关于妥瑞氏的演讲,十二三年的时间里,曾琮谕做了1000多场。而在此之前,因为妥瑞氏的影响,他曾在初中时遭遇校园霸凌,并因此轻生。幸运地活下来后,他决定要去讲述自己的经历,让更多人理解和尊重生命的个体差异。
伴随着这些“众目睽睽”下的讲述,他们将自己的疾病一次次地“曝光”,扯开了一条让妥瑞氏患者接入普通生活的口子。
很多妥瑞氏患者都在寻找那个融入社会的“口子”。对于一个容易被“特殊看待”的疾病亲历者,我们很想知道,那些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限制的人背后有着怎样的支持?那些被卡住的人又正在经历什么?他们仍在试图做着怎样的尝试和努力,有没有再向前一步的可能?
好笑段子的背后
“我自己一个人去玩鬼屋,被安排跟陌生的玩家一起组队,拼船拼车。黑暗的灯光下,我在人群里面一抽(动),他们就开始跑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?也跟着跑,追他们。我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越紧张抽得越厉害,所以我就一边追一边抽,前面的人就跑得更快了。”
这是讲脱口秀两年来,蛋挞最炸的一个段子。当然,在台上表演的时候,他也伴随着妥瑞氏带来的抽动,比如说甩脖子。不过这些对他而言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要让观众笑。
刚开始讲与自己的妥瑞氏有关的段子时,蛋挞会担心观众会不会感到不适,或者“不敢笑”。如果感到现场观众有些拘谨,他上台时会先多讲一些“碎梗”活跃一下气氛。比方说:大家今天可以笑,不用害怕,也不用心疼我,要这样想,你们要是不笑,光我在台上抽就显得很尴尬是吧?
这些与妥瑞氏有关的段子,都来自蛋挞的真实经历,其中大概10%的内容经过了喜剧化的加工。随着一遍一遍地在脱口秀舞台上讲述自己的经历,他发现自己也在经历着与自我以及妥瑞氏的和解——那些曾经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记忆,通过喜剧的方法,在某种程度上变得“正向”,这也使得他更愿意去“默认当时就是这样了”。
在蛋挞构思的新脱口秀段子里,要讲的是他初二时曾在脑科医院住院的事。而实际上,2012年住院的那三个月,是蛋挞在妥瑞氏中经历的“最黑暗”的时期。
那时,在妥瑞氏的影响下,他开始控制不了地咬舌头,咬腮帮,甚至把腮帮咬穿,患上了败血症。他记得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,嘴巴里塞着药棉,身上很多地方都吊着液,连着管子。最初的一个礼拜,他每个晚上只能睡着30分钟,因为“开始长肉就会疼醒”。
妥瑞氏综合征是一种从儿童时期开始、以多发性身体和声音抽动为主要特征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。其主要症状包括进行无意识的压抑不住的动作和发出无意识的声音,通常会在青少年时期达到高峰。
对我国1992年至2010年的13项流行病学研究荟萃分析显示,妥瑞氏综合征的患病率为0.3%。我国现有20%以上的人群处于0~18岁年龄段,这也意味着未成年的妥瑞氏患者约达200万。
对于曾琮谕而言,妥瑞氏是在10岁开始跑出来的,他的“黑暗时期”也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。那时正在台湾读国三的他,因为妥瑞氏带来的问题,在学校遭遇霸凌。“觉得没办法渡过,一片灰暗,自己对自己也是不接受和厌恶。”曾琮谕说。当有一天,同学把拧断水笔的墨水泼到他身上时,他的忍耐到了极限,从4楼跳下,但幸运地掉在了一辆汽车的天窗上。
在整个社会适应的过程中,妥瑞氏首先会给亲历者在学生时期带来极大的挑战。
宋华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出现挤眉弄眼的抽动症状,并逐渐加重,伴随着幅度更大的肢体和声音抽动。宋华煜今年20岁,从小生活在山东寿光的村镇上,在他的记忆中,小学时,他遭遇过同学的辱骂并爆发过肢体冲突。初中也是勉强上完,他感受到自己不受学校欢迎,被排挤。初中结束后,他没有再去上学。
今年17岁的妥瑞氏患者小健,学历只停留在小学。可事实上,他读了小学、初中和职高,但在这几个求学阶段里,他都没有读满。他记得自己上学时经常坐在最后一排,“感觉去了啥也学不到,而且还会被同学们嘲笑”。再加上自己当时比较胖,很自卑,一直到现在,他最大的愿望都是“能交到几个朋友”。
由于每个妥瑞氏亲历者的症状严重程度不一,他们的遭遇也因此各异。生活在四川的腾珠在症状开始爆发前,只是表现为眨眼睛,高中毕业后,忽然家人对她说:你这个(抽动)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响。大二时,她才知道自己患上了妥瑞氏,并一直读到研究生。虽然妥瑞氏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学业,但她一直很自卑。
上高中之前,虽然已经开始伴随着妥瑞氏的眨眼、耸肩、扭脖子、甩手等症状,但张晓雯一直都能应付这些影响,成绩好,与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不错。但到了高中,药物的副作用让她在学校里变得嗜睡,很难集中精力听课,成绩开始下滑。在恶性循环的漩涡里,她发觉自己开始成为班上“被讨厌”的那个人,甚至被“劝退”过。
但张晓雯还是读完了高中,并且上了大学。她的手里一直抓着一样东西。
破茧
“我非常享受那种引人注目的感觉。”张晓雯说。但这种注目不是由妥瑞氏带来的关注。她想做一个主持人。
主持人和妥瑞氏看上去是一组矛盾的组合。但张晓雯从高中开始就有了这个想法,“我希望别人注意到我不是因为我的病,而是因为我足够精彩。”一些妥瑞氏患者在采访中讲述到,在专注做事的过程中,妥瑞氏的症状可以得到短时的一定程度上的压制。
张晓雯考上了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,但挑战也越来越大。进入大学之后,她身上的症状开始加重,还出现了一些“很奇怪”的强迫症状,比方说,很用力地拍自己的头,或者别人的头。这些行为她也可以短暂地压制,但压制过后,它们会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,总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爆发出来。
《中国抽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解读》中指出,约50%的妥瑞氏患者一生中会共患强迫障碍,此外还有可能共患注意力缺陷障碍、学习困难、焦虑、抑郁等共患病。
张晓雯的主持人之路从在超市促销牛奶开始。有一两次,她穿着高跟鞋在超市里促销了12个小时,却没有收到说好的500块工钱,“人家明确跟我说,你说话怎么老在打梗”,钱被扣了。
2020年,大学毕业后,她有机会去主持抽奖一类的商业活动。张晓雯喜欢这种互动性强的主持,因为需要走动,或者和大家招手,就算有抽动也不会被发现。上班后,她也会在每个周末接单子,主持一些活动,她尤其喜欢主持小朋友的生日宴,因为对她而言更简单一些,会让她很有信心。
但主持这件事一直都只能作为张晓雯的副业。日常的求职之路对于她而言并不顺利。毕业后,她去了一个婚礼策划公司,在前台工作,由于长期服药,那时的她仍有很严重的嗜睡,虽然老板应聘时接受她的妥瑞氏症,但一周后还是把她劝退了。
接下来是两份家人介绍的工作。一份是做了4年的金融业的文员,她讨厌这份工作,觉得作为“关系户”在这里上班,体现不了自己的任何价值。期间她一直试图自己去找其他工作,但没有成功,就一直干到这家公司垮掉。另一份是在一家婴幼儿机构里做线上运营,因为人际关系上的问题,在只干了一个多月之后,今年6月她选择辞职。
她觉得自己像活在一个茧里。而破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在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之前,蛋挞也尝试过很多事。2020年,大专毕业后,学音乐教育的他做了几个月的启蒙音乐教育代课老师。那时,老师给了他一些学生客源,有人能理解他的抽动症状,也有些家长会介意。后来,他开过电子烟专卖店和零食超市,但都做了一两年就关掉了。
2022年底,正在父亲介绍的一家口香糖公司里做业务员的蛋挞,在老家马鞍山看了一场脱口秀开放麦。这是他第一次看线下脱口秀,“感觉很有意思”。不只是脱口秀,小品、相声都是他喜欢的,还喜欢给朋友讲笑话。
他当场报名参加了第二天的开放麦。那之后,他开始了早八晚五上班,下了班就坐高铁去南京或芜湖表演开放麦,晚上再坐高铁回马鞍山的生活。
2023年,“为爱发电”了半年左右,蛋挞接到了南京俱乐部的一个稳定的商演。他辞掉了业务员的工作,成为一名全职的脱口秀单口演员。
“突然找到了属于我的一条路的感觉”,蛋挞说。他觉得自己运气很好。此前,妥瑞氏一直都是他身上的那个“弊端”,而在脱口秀舞台上,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“优势”——他有很多经历作为素材,并且它们还一直源源不断地发生着。
曾琮谕与妥瑞氏的故事也一直在发生着。从4楼跳下,幸运地被汽车天窗接住的他,经历了全身粉碎性骨折,在床上躺了两年。“我当时想自己既然活下来了,既然上天不带走我,要么我就(只是)幸运,要么就是我还有可以为妥瑞氏症贡献的地方。”曾琮谕说,“15岁之后,我才慢慢思索我的人生。”
坠楼之后,曾琮谕的妥瑞氏症状非常严重,“又抖又叫又骂脏话”——妥瑞氏症又叫抽动秽语综合征,严重者可能表现为无意识的、压抑不住的粗鲁或冒犯性的言语。于此同时,很多妥瑞氏患者又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愤怒,会气自己为什么要这样,为什么忍不住?
那时曾琮谕的父亲并没有选择让他在房间里冷静,让这些症状“降温”,而是把他带到了人多拥挤的大卖场或是百货公司。
曾琮谕记得,当时爸爸只跟他说了一句话:如果当你不舒服的时候,你只想要待在你舒服的地方,那以后我们都不在的时候你要怎么办?
他无法理解,觉得父亲很“变态”,是一个怪物。
可控与不可控的
当上了大学,开始一个人在外面生活时,曾琮谕开始慢慢理解父亲当时的用意,“原来他是想要让我知道,就算有任何的挑战都要去直接地面对它,不要一个人躲在你自己觉得很舒服很安逸的地方,这是解决不了事情的。”曾琮谕的父亲后来因为罹患癌症去世了。
从大三开始,曾琮谕开始到台湾各处去做关于妥瑞氏的演讲,向老师和学生讲述自己的故事,希望能让更多人理解和尊重生命的个体差异,认识到特殊需求的群体,“我不要让很多人走我之前走过的路。”
他不再觉得妥瑞氏的病症是一种羞耻,“如果我自己不能够先接受我自己的话,别人怎么会接受我,怎么会同理我?”
还在读本科时,曾琮谕考下了游泳教练证,毕业后可以去做救生员。他一直担心自己胜任不了其他的工作,觉得救生员这个工作太适合自己了——是动态的,在那个场所里没有人会关注到他的症状。
他开心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位老师,但却被对方当头棒喝。老师建议他继续读书,提升自己的学历。那之后,他在台湾中山大学读了社会学硕士,后又去美国读了公共卫生专业的硕士。现在曾琮谕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做科研相关的工作,尤其是对妥瑞氏综合征的研究。
在曾琮谕发表的一篇名为《“社会挑战下的心理健康”与“应对机制中的支持系统”:对中国三地妥瑞氏症成人的质性研究》中,他试图去探讨妥瑞氏患者们是怎样克服逆境的,他们有怎样的支持系统?而那些被卡关的人,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顺遂?
在蛋挞看来,他的幸运在于,在整个学生时期,他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对他都是包容的,总会有同学愿意和他一起玩。家庭支持对他而言也极为重要。蛋挞的母亲曾经会因为他的病情有很大的情绪波动,焦虑会挂在脸上,也会直接传递给他。在蛋挞上初中时,母亲开始学习心理学,并成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
当母亲稳下来自己,蛋挞也感受到安定的力量。在一些换季温差大导致症状严重时,母亲会告诉他:没关系,很快就会过去。直到现在,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,蛋挞也会找母亲聊聊天,“她能给我一个安心的情绪”。
那些被卡关的妥瑞氏亲历者在经历些什么呢?
宋华煜正被“卡”在山东寿光的小镇里。初中毕业后,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“憋”在家里。有时路过镇上的快递点,他会去打听能不能找份活,但站点的人怕他的抽动症状被顾客投诉。
今年年初,在家里待了6年后,19岁的宋华煜被同村发小的丈夫叫去自己的店里做货车装饰学徒,一个月800元。他不图钱多钱少,主要是能从家里走出来,有个事儿做。老板觉得他虽然社会阅历浅,但心眼不坏,对他也很包容。
但刚做了三个月,另外一个学徒就把他打了。因为一些琐事,当宋华煜出现强烈抽动症状时,对方猛地拍了他的头,宋华煜说:“你再拍一下试试!”对方起身走到工具箱旁边要拿东西。
老板把他们拉开了。宋华煜的父亲得知情况后,让他马上回家。他在给父亲的微信里说:我可不想一巴掌直接给我拍回原形。宋华煜说的“原形”是那种整个人烂透了的感觉,从过去一直到现在,被妥瑞氏影响的学业、人际交往、青春,都是灰白色的,沉重的。
他特别想走出去,走出他和妥瑞氏对决的“八角笼”——在这持续的对决中,他始终在激烈反抗。他一直强调必须要让自己处在一个认知清醒的状态,理智地去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,他不想被阴暗吞噬。
他也想逃离现在的环境。从家往南走一公里有妈妈工作的钢铁厂,往北开车半小时是爸爸工作的板厂,跟钢铁厂是一个集团,但他很难在这些厂子里找到活干。他也不想再靠这些厂子养活自己,“不能我们一整个家都靠这个集团养活”,宋华煜说,“我还年轻,我得自己出去。”
在今年四月上映的《我和我的妥瑞氏》这部纪录片里,宋华煜出镜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他希望更多人能看见自己,希望也能扯出自己的那一道融入社会的口子。
他现在也更能理解他人。拍摄纪录片后他认识了一些“妥友”,他发现,当有妥友在他身边突然无征兆地叫了一声时,他也会被吓一跳。“我才20岁,有时像中二热血少年,有一往无前的勇气,但我也觉得清醒和理性特别宝贵。”
17岁的小健,减肥成功后,多了些自信,现在开始在叔叔的台球厅里学做一些事,比如说做短视频,他也喜欢这件事。但更重要的是,他要先学会表达和沟通,像是口头总结今天做的事情,以及明天的计划。刚开始他的大脑会一片空白,上学时,他从没站在台上发过言。他一直发愁自己的小学学历,但现在他想先学一些东西,也许以后可以自己开个店。
今年25岁,硕士毕业的腾珠,虽然症状比较轻,但在毕业后的两年内她经历了两次工作劝退。现在她正在考事业编的工作。
张晓雯的主持人之路在渐渐收窄。两年前,随着症状的加重,在用遍所有的方法后,她决定去做DBS(脑深部电刺激)手术,在胸前和大脑皮层安上了两个电极来抑制她的神经反应。虽然这个手术对一些患者有作用,但在她身上却没有什么效果。
她还是会有逐渐加重的症状,也无法像以前一样能在舞台上把症状压制很长时间。“别人只要跟我在一起两秒钟,就会发现我有问题”,张晓雯说。尤其是一些强迫行为,比如,说一些奇怪的话,做一些奇怪的表情、行为,这一方面让她的身体感到很疼很累,另一方面,也会更加不容易被理解。
接下来,她打算尝试做直播。“看我直播的人,是为了看我的妥瑞氏”,张晓雯说。会有妥瑞氏患者的家长来看她的直播,他们好奇她作为一个妥瑞氏患者是怎么做主持人的,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也可以不被局限在那个茧里。但有时她也会遭到恶意的声音,说她是骗子。
小时候,只要有人提到抽动症三个字,张晓雯就会哭,甚至写到“抽动”两个她都会嚎啕大哭,觉得别人在看她,笑话她。但现在她不会了,“我不想蒙骗自己,我想把它承受,然后结痂。”
在蛋挞的一个视频账号上,他上传了一些自己脱口秀演出的片段。排在这些视频最前面的,叫做《妥瑞氏症是什么?(所有视频前提)》。蛋挞一直希望,如果有人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抽时,会想到自己的那个视频——这个人可能是妥瑞氏症,然后就不再去关注这个人了。
现在,蛋挞在准备自己的第一次脱口秀专场巡演,想再往前走一步试试。他心里也会有一些担忧,比如说,他也有妥瑞氏症中秽语的症状,如果自己在演出时没控制住,有人会介意怎么办,会不会有严重的影响?
虽然妥瑞氏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他做脱口秀演员的“优势”,但也许到后面也会出现一些“劣势”,因为“它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部分”。而对于妥瑞氏的一些更深层的感受和思考,蛋挞觉得,它们可能很难变得好笑,成为舞台上的段子。
【版权声明】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【北青深一度】所有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。



 与君说事
与君说事
 寒士之言本尊
寒士之言本尊
 启视说
启视说
 奇观历史君
奇观历史君

 蒋飞Talk
蒋飞Talk
 江月白
江月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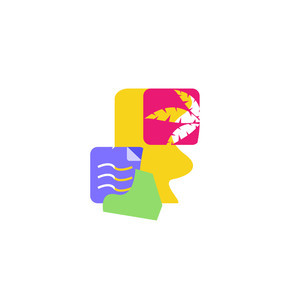 情报熟了
情报熟了
















 豆莱说
豆莱说




